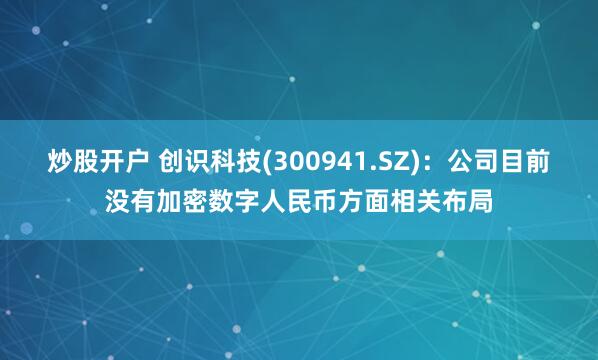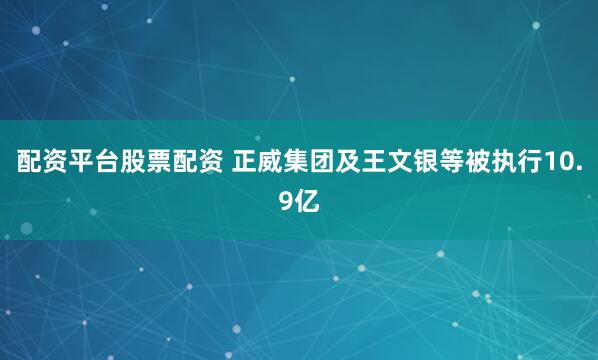公元前221年专业炒股配资网站,秦王朝刚刚完成天下统一,法家代表人物李斯位居朝廷要职,却因为一次被嬴政责备而惊得汗流浃背。要理解这一幕,需要回到嬴政为什么要改变称号,以及李斯在秦国的崛起与最终结局。
嬴政完成统一后,不满足于“王”这一称呼——他不愿与周朝的文王、武王或上古的大禹、商汤相提并论,想要一个全新的、前所未有的至高称谓。咸阳宫内灯火通明,群臣翻阅典籍、争论不休。李斯独自站在窗前,望着寂静的大地,他清楚皇帝心中早有倾向,关键是把那称呼猜出来。
众臣最终建议用“泰皇”——古人曾有天皇、地皇与泰皇之说,泰皇被认为最尊贵。但嬴政当即否决,改用上古的“帝”字与“皇”字结合,定名为“皇帝”,并自称“始皇帝”,意在成为千秋一统的开创者。自此“皇帝”成为至高无上的代名词,沿用两千余年未改。
展开剩余82%嬴政建立大一统的秦帝国时,李斯是不可或缺的谋士。李斯出身上蔡,早年只是基层文书,但他好学,30岁投师荀况,学成后又受韩非法家影响,最终形成了自己务实的法家思想。他选择投奔秦国,不是盲目追随强权,而是因为秦国的变法与法治思想与他契合。秦国通过重赏取信、商鞅变法、废礼立法、重赏军功、强化中央集权,迅速提升了国力与社会生产力,成为李斯施展抱负的沃土。
李斯进入秦廷后,积极建言献策,得以受嬴政重用。他向秦王提出兼并六国的策略:暗中笼络对方权贵,必要时以重手解决眼中的障碍,然后以武力统一天下。嬴政识才,任用李斯,在十余年里秦国版图不断拓展,李斯的功绩与地位也水涨船高。公元前221年,齐国正式降服,春秋战国五百余年的战乱终结,百姓得以返家安居。这一年,嬴政实现霸业,并刻制国玺,李斯用小篆书写铭文,为帝国的制度化奠定文字基础。
获得天下只是开始,如何治理新帝国更为关键。李斯主张将六国贵族富豪迁往咸阳,一方面便于监管,另一方面能促进都城经济并改变民众的生活方式。他提出的郡县制,取代分封制,将中央权力延伸到地方;统一小篆文字、统一铸币“秦半两”、统一度量衡、建立三公九卿与郡县官僚体系、实行以户为单位的户籍与税赋制度(即“编户齐民”),这些举措将国家机器化、制度化,大大巩固了皇权,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。
然而,制度的强硬推行也带来反噬。六国旧俗与民众思想并非一朝可变,秦政高压治理在稳定秩序的同时,也埋下不满与隐患。公元前210年,50岁的嬴政在第五次巡游中病重。在沙丘,嬴政给长子扶苏下达密诏,命其交出兵权回咸阳主持葬礼。《史记》记载,赵高作为中东府令和印玺掌管者,密封了这道诏书,却未将其送出。随后,始皇驾崩,赵高与权臣密谋,封锁消息,回咸阳后假借圣旨逼扶苏自尽,扶持纨绔子弟胡亥即位。
胡亥登基后,权力斗争加剧。赵高先拔擢又排挤异己,李斯作为前朝重臣屡次上书规劝,但终因政局复杂、被赵高诬陷谋反,遭逮捕受刑,公元前208年7月,李斯被腰斩身亡,家族亦被株连灭族。曾经位极人臣的谋士,最终落得惨烈结局,这在后世引发许多非议与感慨。
对于李斯为何没有力挺扶苏、反而在胡亥篡位中扮演何种角色,史家与后人有多种判断。有人把李斯描绘成“利己主义者”,借《史记》中“仓鼠与厕鼠”的寓言来指责他见利忘义,但这种断言过于简单化。实际上,李斯能从基层成长为能人,靠的正是文化与治事才能;他信奉法家,但也吸收了多家思想,强调的是国家治理的务实方案。李斯之所以在秦朝位列显宦,一方面因他与嬴政志向相合;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当时读书人以功名与政治实践为价值取向,名声与成就往往高于身家性命。
至于扶苏,司马迁称其仁义、刚毅、有勇武,但在关键时刻扶苏接受诏书自尽,不辨真伪,也让人怀疑其政治智慧与处事能力。扶苏更倾向儒家治国,而始皇与李斯倾向法治,此种理念分歧在当时难以调和。蒙恬与蒙毅兄弟深受嬴政信任,扶苏被派往边陲监督军务,显示出始皇晚年对人事布局的复杂考量。若始皇真欲立扶苏为嗣,理应在安排与现场安排上更明晰,事实并非如此,因此也有人推断嬴政原本并非要改立扶苏。
综上,我倾向认为嬴政并非简单地将皇位传给扶苏,历史记载中存在模糊之处:负责丧事并不等同于立为继承人。若嬴政本意偏向胡亥,这也能解释李斯后来为何在新政权中失势并遭诬陷——权力更迭常伴随“过河拆桥”,秦朝初建时那些立国功臣如商鞅、张仪、李斯,最终都未能逃脱被清算的命运,也是“一朝天子一朝臣”政治常态的残酷体现。
李斯的一生,从布衣到相国,再到身首异处,充满了时代赋予的机遇与风险。他既是实践家,也是制度的缔造者;既为秦的强盛立下汗马功劳,也在权力斗争中败下阵来。这段历史提醒后人:政治与制度固然重要,但权力的更迭与人心的复杂,最终会决定个人的结局。
发布于:天津市易倍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